《史记》被誉为“史家绝唱,无韵”。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的开创性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历史写作方式上,还体现在他选择史实的独特标准上。《史记》收录心理文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巨鹿郡守尚晨在汉高祖十年(197年前)发动叛乱,刘邦亲征期间,吕后引诱并杀害了疑似掌管尚晨的韩信。《淮阴侯传》记载了刘邦对韩信之死的心理活动:“汉高祖从军而来,见信而死,既喜又怜。”

太史公用“喜”和“悲”这两个字来描述李渊的情感和心理,由此引出了历史上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心理写作能否成为历史写作的必要内容?心理写作如何才能有足够的“理性”?这似乎需要从理论上来理解。
从根本上说,“历史只是人们追求自己目标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是历史舞台上始终如一的主角,他的活动是历史研究的永恒焦点。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人出现后在世界上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和痕迹应该被纳入历史范围;从民族兴衰到最普通人的习惯和感受,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是,任何人类活动都必须伴随着相应的心理活动;人类的一切外部行为都与内部心理活动有着天然的联系,二者密不可分。既然人的心理活动是历史活动的自然组成部分,那么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写作就应该涉及人的心理活动。

然而,人类思想和心理活动的隐秘性决定了历史心理写作的巨大难度和特殊性。如果历史学家对人的外部活动的研究能够通过多重证据确信自己基本上能够满足“客观性”的要求,那么对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研究必然会失去很多自信。
心理活动的隐秘性造成了证据的特殊性:第一,证据是隐藏的而不是呈现的。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虽然客观存在,但在很多情况下不一定会留下痕迹供后人研究。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学家根本无法获得具体的证据,他们必须根据个人经历来推测所研究的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因此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在正常情况下,出现在历史编年史上的历史人物的话语,往往被后人用来作为当事人心理活动的证据。但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的“言”与心理活动即“言”与“心”的不一致之间存在张力,导致语言证据的证明力不足。历史人物的“不真诚”,甚至不真诚的言辞,随处可见。有太多的人用皇冠的话来掩盖史实,或者兜售自己的自私和奸污。再次,“行动”的出现与“心”的真相相悖,史书所包含的外在行动不足以洞察历史人物的内在活动。所谓“周公畏八卦日”,当王莽谦恭不篡。谁知道你人生之初会不会死?”这些因素决定了历史心理写作的难度,使得历史写作中所谓的“心理真实”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既然历史心理学的写作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和局限,如何才能在不丧失其“合理性”的情况下写作?「理性的极限」在哪里?太史公的历史心理书写似乎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毫无疑问,汉高祖心中会对韩信被杀产生一些感情,从而引发相应的心理活动。但他在这件事上的具体心理活动,绝不会向别人表达,也不太可能在公开场合向别人透露。换句话说,太史公不可能有机会了解到他心理活动的直接具体证据。那么,太史公描写汉高祖“爱与爱”的心理活动的依据是什么呢?难道太史公不担心后人指责他主观吗?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熟悉了这段著名的文字,但没有人认为太史公记住的不是汉高祖真实的心理情感。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不止一个,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符合历史心理学写作所要求的“理性”。

那么,历史心理学写作在哪些维度上是“合理”的呢?
首先是人性的维度。“人来自动物界的事实决定了人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是或多或少的摆脱,而且是动物性和人性的区别。”(恩格斯:《反都灵论》)历史上个人行为的动力是个人欲望,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构成了人类历史。在每一个生命体表现出来的兽性中,人和其他动物一样,被认为是超越动物的。换句话说,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思想的控制下,由动物的欲望驱动的;动物欲望,恩格斯称之为“动物性”,是所有人心理活动的共同底线。这就是“所有人都有一颗心,所有人都有一个理由”的人性法则的基础。因此,基于人性的刻画是历史心理写作合理性的最大和最基本的维度。

在太史公的笔下,刘邦和韩信都有“人”的爱好和情感。作为一个人,刘邦对韩信的死是绝对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心有所觉”是必然的,但“觉有所觉”的内容因时间和情境的不同而不同。但不管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在以皇帝为中心的家庭和世界的格局中,他们的感受一定是以利己为中心,以自我欲望为导向的。“只有人生来就有欲望”,历史人物的心理书写是以人的欲望为基础的,其有效性是以人的欲望的客观存在为基础的,因此具有普遍适用性。《史记》记载了项羽和刘邦亲历秦始皇之行的情景,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个说:“一个可以代替另一个!”一个说:“啧啧!君子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不同的反应并不能改变共同的欲望方向。正如鲁迅所说:“余要什么?就是拿国家说‘所以’。.....什么是“所以”?一言难尽;简单来说,就是纯粹的动物欲望的满足——付伟、孩子、玉和丝绸。”(《热风·情·录·五十九》)显然,鲁迅对刘翔心理状态的判断是建立在一个原则上的,那就是客观的人的欲望,即追求“为夫、为子、为玉、为丝”的满足和享受。这就是太史公所坚持的心理写作原则。

虽然人类的心理活动是以永恒的人性为主导的,但是从人性的维度去写历史人物的心理毕竟太宽泛了,很难完全解释个体的心理活动。人的具体行动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赋予的角色,人的心理活动始终与社会角色有着根本的联系。俗话说:“宫里的人想的和茅屋里的人想的不一样。”时代和社会角色应该是历史心理写作的第二个维度。
对于韩信之死,其他在刘邦手下为天下而战的将领的心理反应可能不一样,但并没有几种情况:要么是被残忍利用的凄凉与恐惧,要么是生存的快乐与疑虑,要么是减少了一个对手的幸灾乐祸,但永远不会是“快乐与怜悯”。“快乐而有爱”的强烈心理情绪只能属于刘邦,属于称王称霸的刘邦,而不是以前的刘邦,是刘邦成为“天子”后的心理反应。如果韩信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意外身亡,刘邦心中的感受大概是“痛并可惜”而不是“喜并可惜”;前者是他作为“裴公”“汪涵”的心理状态,后者是他作为“天子”的心理感受。

韩信的成就让他担心自己的皇位,他忍不住失眠。如蒯通所言,以韩信之功盖世,略出天下之才。“戴震掌握大权,不赏功德,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皆惊矣。”。刘邦登上台后,最需要的是建立君臣秩序。韩信的存在是一大障碍。因此,当他听说吕后已经消除了心中的大烦恼时,他怎么会不“高兴”呢?
但是“可怜”的感觉从何而来?这当然是因为韩信为他打败了项羽,获得了很大的地位,为他的帝王生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还不是全部。还有另一面。刘邦对韩信是高度警惕的,但是韩信所谓的“谋反”很大程度上是“有罪推定”,并没有真正的证据。刘邦由“齐王”降为“楚王”是以防万一,而他由“楚王”降为淮阴侯的借口只是“民告公”。在没有韩信谋反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刘邦不禁心虚,感到“可怜”。第二个。第三,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刘邦登上皇帝宝座,统治天下。但是,他在皇帝宝座上面临的局面并不容易,他需要人才来辅助。刘邦回到家乡,与父子俩纵情饮酒,慷慨悲怆。他为自己唱道:“云起风飞,贾伟海归故里,勇者镇守四方!”面对帝国工业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对优秀人才的需求,像韩信这样的人才都死在女人手里了,他怎么能不生出“怜惜”呢?

除了人性的维度和时代作用的维度,人格是历史心理写作的第三个维度。不同环境造就的不同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特征。“爱与被爱”的复杂情感体现了刘邦的人格。在传统社会中,反叛者夺取大位后屠杀英雄,是权力的欲望和实现家族权力垄断所采取的手段,可以说是皇权制度的“客观”要求。但是同一个屠杀英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大概是不一样的。就朱元璋而言,杀英雄带给他的感情恐怕更多的是“喜”而不是“悲”。清代历史学家赵翼说:“(明祖)以天下人之功取天下,天下定之时,以取天下人之谋杀之,其残暴前所未有。丐帮熊猜到了,自然要杀。”“自然好杀”恐怕有点夸张。朱元璋杀得好的部分原因是早年受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虐待,积累了太多的仇恨,造成了心理创伤,产生了变态的心理。

刘邦家境不差,至少温饱不是问题。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养成了“不做家里的生产活”和“好酒好色”的习惯,以至于被父亲称为“流氓”,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懒。在秦末大乱的背景下,被推上反秦之路,逐渐成为争夺中原的关键人物。但在他心里,却是一个社会“流浪汉”角色:敢做敢为,无视道德,善于算计,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在逃跑的路上,他追赶储君,把自己的孩子推出车外;面对项羽威胁要煮刘的父亲,他并不介意,甚至想“给我一点运气”;楚汉同意以缺口为界停止战争,但违背诺言,发动突然袭击。他羡慕秦始皇,认为“君子当如是”;直到为王,他威胁他的大臣发誓"不做刘的王,但整个世界将与他战斗"。这一切都说明,他的性格和信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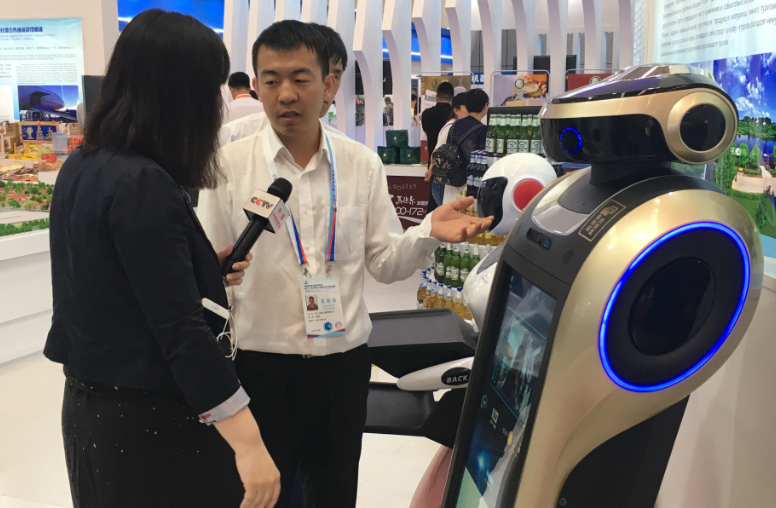
对于这样一个在权力上孜孜以求的人来说,看到韩信落得如此下场,必然会把自己放在韩信的位置上,做出“自己推别人”的假设。韩信被萧何誉为“独一无二的国士”,刘邦也感叹他的军事才能。韩信为刘邦策划了三秦“引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胜”的战略,消灭了魏、戴、燕、赵、齐,最终与刘邦会师,消灭了项羽,最终成就了刘邦的帝王生涯。尤其是在楚汉之争的决定性时刻,韩信凭借自己雄厚的资本,“右投是汉王的胜利,左投是王胜”,也可以自立为王,拥有三条腿。但是,他觉得刘邦“脱了我的衣服,推了我吃饭,听了我的话”,却不忍自举大旗,带头,犹豫了一下终于站到了刘邦这边。鉴于刘邦不道德、心计、胆大的性格,他岂不是对不起韩信的“天尊取之,而咎由自取”?在霸权触手可及的关键时刻,韩信并没有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规划,坚持“坐车的人载人,穿衣服的人看人,吃人的人死”的道德信条,缺了一只千载难逢的好手,直到死,他才想起那句老话:“狡兔死,好狗亨;高鸟竭,好弓藏;敌破,谋臣亡”,最后死在一个死女人手里。这一切怎么能不让刘邦心感受到情感,却以同情和遗憾生出“恻隐之心”?

太史公的典型例子表明,心理写作不仅是完整生动的历史写作所必需的,而且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心理写作的合理尺度。这是我们从阅读《史记》中得到的启发之一。
作者:张旭山
来源:中国阅读报
来源:吉林福音时报
标题:(文化)韩信被杀后刘邦的心理活动
地址:http://www.jxjgzhdj.cn/jlxw/287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