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张爱玲论写作:没有一出戏能够用快乐为题材
本篇文章3493字,读完约9分钟
我读中学的时候,老公对我们说:“大惊小怪,一定要好好开始,好好开始,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结局一定要更好,一定要反响好才能有余味。我们都点头表示理解。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更好——我们还没来得及说出原因,就已经放声大笑了。
然而今天,当我写完一部小说,抄完,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摇摇头撕了起来,想到老师的话,我不禁感到难过。
写作真的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吗?写作只是表达观点,说话也是表达观点。写文章不一定比说话难。古代没有发明纸墨,珍贵的记录和说明都用漆写在竹简上。程序极其繁琐,人们很少有机会以书面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作风简短含蓄,不允许胡说八道。后来有了纸和笔,就可以摇一摇,慢慢瞎说了。现在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写文章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没必要再郑重声明了。最近(1944年)纸张短缺,上海的情况略有变化,作者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论文的问题只是暂时的,基本问题是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无话可说,没有写作习惯的人则无话可说。我不是说很多天才会默默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天才更重要的是普通人。一般来说,过了半辈子的人,大多都有一点真实的生活经历,有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没想过要写下来,但是事情变了又消失了。也许是名言,也许只是没有足够分量的搞笑插入。然而,这毕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损失。比如我认识一个老婆,是一个普通的典型老婆。她对老年人脱发有着非常微妙的观察。她说:中国老太太以前是秃头,现在不秃头了。而父亲,以前是秃头,现在经常秃头。外国老太太不秃,父亲秃。为什么?根据研究,我们得出结论,旧社会的中国女性发髻太紧,头发向后拉得很痛,所以容易秃顶。男人以前没有戴帽子的习惯。现在的中国男人和西方人,很多年都离不开帽子。戴帽子对他们的头发健康有害,所以秃顶逐渐增多。但是外国女人也戴帽子,为什么不秃头?因为外国女人的帽子大小不一,压在眉毛之间,钉在后脑勺上,总是会改变位置,所以不会影响头皮的青春活力。等等,有很多话值得记住。如果专业文人说,我不敢公然抄袭,但是如果他们不靠这个吃饭,他们说算了,我就像捡垃圾一样捡。

职业文人的病,过度表现在自我表现上,以至于无病呻吟,而普通人则嫌不够烦。年轻的时候,他敢说话,但没人理他。中年,他在社会上有地位,说话也有相当分量。大家都愿意听他的,但他却在努力学着做人,一味的忽略负面,说话说话,避免冷淡,总是挑那些深谙的。等老了退休了,就不负责任了,可以畅所欲言了。可惜老人老是唠叨,人也没耐心。你要是讲道理,就会充耳不闻。这是人生一大悲剧。

真正缺听众的人可以去教书。在演讲厅里,你可以扮演空,谁打呵欠,谁就会被扣分——没有更多的乐趣。其次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人吃饭,这样人家就忍不住放弃了,听听你的大话,推断一下世界大战什么时候结束,或者追溯一下你的初恋。
《笑林广记》里有个专门给别人写粉丝的人。这一天,我看到朋友手摇白色折扇,马上拿走给他写。朋友跪了下来。他帮他说:“写粉丝不需要太麻烦。为什么送这个礼物?”朋友说,我不是要求你写,我是要求你不要写。
听说从前有学者被人讨厌,给了钱让他们不写了。像我这样缺乏社会意识的人恐怕享受不到这种幸福。
李礼翁(李煜)在《我送我的闲暇》中说,有一种方法可以骗大师赢。在开本之初,当有奇怪的句子令人眼花缭乱时,其中一个人很惊讶,不敢放弃。文末,灵魂被阿谀俘获,便流连于卷。如果难以区分,也会采用这种方法。好像接近虞姬的方式是惊艳,炫,哄,妖媚,稳重。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讨论作者和读者的关系。
西方有句成语,诗人自言自语,被世人偷听。诗人写诗纯粹出于自然,脑子里一定没有其他人。然而,一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强烈警告我们在写作时避免与自己交谈,并始终考虑读者的反应。这样更安全,除非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例外的巫师。
迎合读者心理。只有两种方式:(1)说别人想说的话,(2)说别人想听的话。
说人家想说什么,就是代表群众发泄怨气。做出改变并不难。但一般舆论往往对左翼文学不满,即脉不开。着急开药方,无非是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思想,就像某个时期的学者谈禅一样。他们不一定听得懂,但大家都能聊,聊得多,聊得精辟。女性很少犯这种毛病,可以说是男人的一种病。这里就不多说了。
退一步写人生的艰难。当然,大家都抱怨这一天不容易,但你总说有多苦,更苦的一些人说:这是什么?更有钱的人也会因为你堵住了他的嘴,让他无法抱怨而感到不开心。
然后,说人们想听的话。你想听什么?越软越好——换句话说,越猥琐越好?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们拿《红楼梦》和《金瓶梅》来打个比方。不考虑他们的文学价值——大众的选择不完全是基于文学价值——为什么《红楼梦》要通俗得多,只听熟悉《红楼梦》的,不听熟悉《金瓶梅》的?但纵观当今的通俗小说,家庭故事并不是浪漫激昂的,而是普通市民的温柔、感伤、道德的爱情故事。所以,用不雅的材料不是问题。

庸俗的味道不应该与色情的味道混淆,但是在广大的人群中,庸俗的味道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你看我的,我看你的,都不行。要想争取到很多读者,必须注意群众利益范围的限制。
作者感到压抑,刻意迎合低级趣味。刻意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大多是有自尊心的,看不到眼里的读者,从而埋下了失败的根源。不要相信他们,想用他们当号召,结果是他们浅薄而没有诚意。读者不是傻子,很快就感觉到了。
要俗,就得从里面打。我们没必要划清界限。我们也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听明成祖的秘史。把自己放在读者群中,自然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给他们想要的,给他们别的——如果作者有什么要给的,拿出来,不用扭捏:这恐怕是普通人无法接受的。那只是搪塞。作者能给多少就给多少。读者尽量多拿。
就像《红楼梦》一样,大部分人在有生之年都读过好几遍。就我个人而言,八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只看到一点点兴奋。每隔三四年看一遍,渐渐有了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个印象都不一样。现在看,只能看到人与人之间诱发的烦恼。——个人鉴赏能力有限,《红楼梦》永远是奉十。
给一个十个只是一个理想和一个标准。大家就事论事,说说写小说的喜怒哀乐吧。想让人哭,首先要让自己哭。如果能好好哭一场就好了,但是我写的悲伤往往属于一种土匪的桓伊。(我的书《倾城之恋》的背景是根据《白舟》这首诗:...有兄弟,不能靠...安安静静的担心,担心自己小。人很多,但是被侮辱的人很多。.....居月,胡迭而微?心中的忧虑就像强盗的桓伊。静静思考。不会飞。),比如土匪桓伊的寓言(喜欢没洗过的脏衣服),我特别喜欢。盆边堆脏衣服的味道恐怕不是男性读者能体会到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悲伤,可以用江南人来形容:心里雾蒙蒙的。(雾二号,普通话里好像没有对等名词。(

如果是故事,那就要有一点戏剧性。戏剧是冲突、艰难和麻烦。即使是p.g.wodehouse(英国幽默小说家伍德豪斯)这样的搞笑小说,也要一步一步引诱主人陷入困境,然后把他弄出来。快乐是兴趣的缺失——尤其是别人的快乐,所以没有哪部剧能以快乐为主题。像《浮生六记》《闺中之乐》《闲情逸致》这种在剧中捶台捶凳自怨自艾的沈也就不足为奇了。

写小说就是给自己制造烦恼。我写小说的时候总是写在某个地方,感觉写不下来。让我特别痛苦的是最近做的《当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吃力的跨过障碍,可以顺流而下,放下去写,故事就结束了。我忍不住自己做决定。.....恐怕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麻烦。宁死也不怕麻烦。麻烦刚刚过去,人也结束了。
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抱怨,但中间我还是认真的开了一些玩笑。为什么一群文人愿意留在文字狱?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文字的魅力。比如我们家有一个老式的红漆行李箱。我在盒盖上发现了这么几行,印成方形:
“高州中同济店开在广东省省会城隍庙左边的老仓巷,自制家用行李箱、衣服、包包、帽箱送客人和食客。请认招牌为“铭记主,不忘光绪十五年”。我站在凳子上,扶着盒盖,看了两遍。因为喜欢,所以抄袭。还有麻油店的条幅和大匾额,都是自己做的,还有芝麻油,卫生芝麻酱,白花生酱,尖锡糖,批发。虽然是现代流行的写法,但似乎和我们隔了一层,略显神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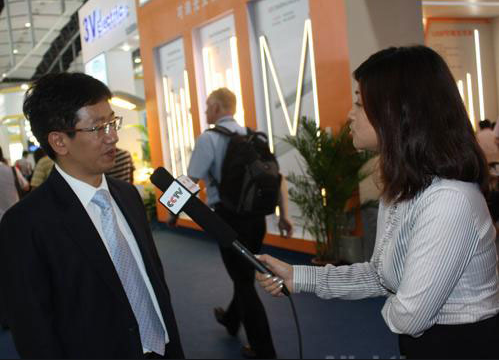
然而,我最喜欢的是屈伸的几个短语:
“即使在三点钟的晨星,民事和军事官员在法庭上。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走。文官写天下,武将上马集干坤..."
像往常一样,这是由首相或战争部长唱的,然后他自言自语,提出了他过去私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果这位女士唱了,她继续讲述自己。不管是老了还是老了,孤王还是丧家,都有着相同的世界观——社会秩序是多么的清白整洁:文官写书保天下,武将上马定做坤!思考让人流泪。
标题:(文化)张爱玲论写作:没有一出戏能够用快乐为题材
地址:http://www.huarenwang.vip/new/20181024/11.html
免责声明:吉林福音时报致力于让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为广大用户提供丰富的吉林今日头条新闻,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吉林福音时报的小编将予以删除。
